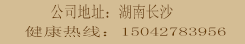![]() 当前位置: 豹子 > 豹子的繁衍 > 故事等我坐拥这江山,必立你为后可她多
当前位置: 豹子 > 豹子的繁衍 > 故事等我坐拥这江山,必立你为后可她多

![]() 当前位置: 豹子 > 豹子的繁衍 > 故事等我坐拥这江山,必立你为后可她多
当前位置: 豹子 > 豹子的繁衍 > 故事等我坐拥这江山,必立你为后可她多
本篇内容为虚构故事,如有雷同实属巧合。
1
那是一个清晨。
我正抱着竹筒在草叶尖收集无根水的时候,一道剑气划破了薄雾,檐下挂着的珠贝风铃忽然“叮叮当当”地响了起来,紧接着,一道火红的身影便闯入了我的余光里。
我还未抬头,一个脆生生的声音道:“风筝渡灵主,我需要你为我画一张皮。”
我没说话,指尖往草叶尖一点,一滴露水便落到竹筒里,“滴答”一声响。
然后我才空出手来,指指一旁柱子上钉着的木头牌子,那里明码标价写着:画皮五十钱一张。
那人干脆得很:“我没有钱。”
我于是不得不抬起头来,见到个红衣黑发的小姑娘,面上还覆了一层白纱。
那是三月清晨里的风筝渡,四围白雾烟烟,绽开的桃色隐在苍茫的雾气之中,将这天地都染成一片粉白。
这本该是个淡淡的暖色,可偏偏她面纱之上露出的一双眼睛,冷得如融雪的空山,生生将这粉白染成了冷色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安歌——也不算是完全见到,毕竟她白纱遮面,我只能瞧见一双眼睛。
可就是这么一双眼睛,虽然冷冽了些,却也足够好看了。
这么好看的一双眼睛,破例一些也不是不可以。
我于是道:“那这样吧,我们风筝渡一向有规矩,没有钱的话,一张画皮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换。你给我讲个故事,故事讲得好了,我也可以为你画一张皮。”
“说一个故事?”
“说一个故事。”
她于是微微皱眉,偏头思忖起来。
“从前,”她斟酌着开口,“从前,我认识一个人,他的话有点多,后来他不见了。”
然后便是长久的沉默。
我:“……”
我:“就没了?”
“没了,”她点点头,顿了顿,似是又想到了什么,补充道,“可能是死了。”
这就有点过分了,我不由得责备道:“这位姑娘,你要是不是诚心想做交易……”
我话还没说完,只听“叮”的一声,寒光闪过,十步之外的那株桃树轰然倒下。
一地落红。
她侧头看我,一双眼中无波无澜,平静得很,开口时声音也是稳稳的:“谁说我不诚心?”
我沉默片刻:“规矩什么的还是次要,主要是我同姑娘有缘,替姑娘画张皮,也不是不可以。”
2
我跟着风筝渡的上一任灵主学习画皮,不久前才出师。
说起我们画皮师一脉,在祖师爷的时代,倒也辉煌过,据说甚至能够生死人肉白骨!
据说大梁之外有个小国,叫做高丽。当年,我画皮师一脉的第十六代传人游历到那,替一个被烫伤的人画过一张皮,谁知这之后,这秘方便被他们偷了去,另起了一个名字,唤作整容。
不过到了如今,画皮其实已经没什么奇特,也就是寻常作画,只不过作画的材料与技法都比较特殊,完成后以画皮覆面,再辅以药水,能使人彻底改换头面,就如同脱胎换骨。
不过如今求画皮者,大多倒不是为了换脸,多半是容貌有瑕,才会重金索求。
譬如我眼前这个小姑娘,她面上虽覆着白纱,可隔着那半透明的白色,其实隐约可见一道狰狞的长伤疤,蜿蜒在她的左半张脸上。
——如此说来,高丽人将画皮称作整容,倒也贴切。
画皮要先打稿。可我铺开画纸,执笔点墨,却迟迟落不下笔。
那红衣姑娘察觉到异样,歪头看我:“怎么了?”
我瞧着她面上挂着的白纱,犹豫半晌,才道:“这位……”
一开口却不知该如何称呼。
她察觉到我的难处,善解人意道:“我叫安歌。”
“这位安歌姑娘,”我道,“你要我替你画皮,总要让我看看你的样貌。”
她沉默,也不知想些什么,片刻后摇摇头:“不必照我的原样画,你随便画一张脸就好。”
我简直哭笑不得:“即便如此,画皮要贴脸,我还得知晓你的骨相。”
这次她反应很快,虽然依旧没什么神情,但人往后一退:“你想摸我?”
我:“?”
我:“我不是,我没有……”
我们画皮师识骨相,只用眼睛看就可以了,不必上手。
可是我话未说完,安歌已经几步窜到我的桌边,抓着我的手隔着白纱贴上她的脸:“摸吧,我赶时间,快一点。”
我:“???”
3
这一笔生意做得实在叫人胆战心惊。
我虽然也不是什么王公贵族,可到底从小背着《礼记》长大的,尤其晓得男女大防,长这么大,姑娘的手都没有牵过,更别说摸人家的脸了。
我简直面红耳赤、心若擂鼓!
但我瞧着安歌,她目光坦荡,神色里并无半分戏谑,大抵真的只是赶时间。
她果真是在赶时间,因为一个时辰之后,我打好稿画好皮,转身去里屋拿个药水的空当,安歌已经不见了——连带着我的画皮。
但是没有上药水的画皮,它就如同一张普通的人皮面具,它……保质期短啊!
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,这一单生意做成这样,我心中难安,战战兢兢,过了半个月,果真有苦主找上门。
彼时我正跪在祠堂给先人们上香,一阵阴风穿堂而过,风筝渡涌进来大批小兵,当场就将我五花大绑。
完了,我单知道安歌身手好、脾气大,却没想到她还是个有权有势的。
我自知理亏,但还是忍不住为自己开解:“只不过是画皮的质量差些,不至于要这阵仗吧?”
那领头人瞥我一眼,一脸“懒得跟你废话”。
我向他身后张望,人群中并不能找见安歌的身影。
我道:“安歌姑娘呢?让她来同我说。”
那人居高临下地睨着我,拿鼻孔出气:“先将你押解入京。那丫头早晚也能抓到!”
我就这样被铐上枷锁、装进囚笼,一路往帝都盛京去。
路上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知晓,安歌原来并非什么权贵,她跑来我这里买画皮,不是为了掩盖脸上的什么伤疤,而是为了易容——去刺杀当朝的七皇子。
刺杀当然没有成功,安歌跑了,而我毕竟帮助她易容,作为从犯,被抓了。
这谁顶得住啊,我不过想做一单生意,却成了杀人的从犯。
我不服,但我没什么办法,我是个艺术生,拳脚功夫不行。
那些官兵将我死认作安歌的同*,没抓到主犯本来就在气头上,不每天给我两顿鞭子就已经是善待我了,说理我也没地方说去。
我只好老老实实呆在囚笼里,一行车队夜以继日往盛京赶,连赶了两天路之后,却忽然生了变故。
那时我正靠着囚车的木栅栏睡觉,忽然不知从哪飞来一只小石子儿落在我的额头上。
力道很大,额头很痛,我当场就痛醒了,睁眼环顾四周,只瞧见囚车不远处有个刚熄灭的火堆,还亮着点点的火星子,守囚车的人却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!!!
眼下正是无人守囚车的时候,我!
我也还是逃不出去。
正沮丧的时候,一只手从我身后伸出来,一把捂住了我的嘴,然后有个声音在我耳边喊道:“画皮师。”
这个清冷的声音我认得,是安歌。
4
来人从身后捂住我的嘴,不过箍得并不是很紧,我得以转身去看她。
果真是安歌,一身夜行衣从头包到脚,背上还背了把大刀。
“守囚车的人被我引开了,”她道,“画皮师,我来救你。”
我瞧着安歌,她也瞧着我,覆了黑纱的面上只露出一双眼,但是亮闪闪的,像只小山猫。
她叮嘱我:“一会儿我放开你,你不要闹出大动静,我救你出去。”
我点点头,于是她放开我,警惕地望了望四周,然后向后退了两步,手放到刀柄上:“小心一些。”
我不解:“什么?”
话音刚落,长刀劈在木栅栏上,随后“哐当”一声巨响,囚车瞬间四分五裂。
安歌瞥我一眼,手起刀落,带着“呼呼”的风声,这次劈开的是挂在我脖子上的枷锁。
枷锁上还带了铁链,碰上刀刃动静更大,简直要擦出火花,“哐哐”响。
我:“??”
我:“不是说好了不要闹出大动静吗?”
安歌:“是啊。”
我:“这动静还不算大??”
我简直风中凌乱,安歌却还冷静得很,她收刀回鞘,又伸手拉我起来,甚至有闲心替我拍去身上的木屑,然后解释:“我并没有找到钥匙,这样便捷些。”
事已至此,多说无益。她拉着我的手还没放开,我反抓住她的手腕,带着她拔腿就跑。
安歌:“你……”
我打断她:“快跑,一会儿他们循着动静回来了,谁也跑不掉!”
安歌道:“这倒不怕,他们就算一起上,也未见得是我的对手。”
她说着,顿了顿:“但是——”
我:“但是什么?”
话音未落,前头遇上一伙人,个个手上执了刀,领头的那个我认识,正是这些天负责将我押解进京的人。
我脚步一顿。
领头人怒目圆睁:“果真是调虎离山——抓住他们!”
说着提刀就砍。
安歌道:“但是你跑反了!”
5
那刀当然是没落在我身上的。眼见着就要劈到我时,安歌将我一拉,不知怎的就和我换了个位置,长刀出鞘,提起就砍。
那间隙我还听她抱怨:“啧,这么快就回来了。”
言语间还有些懊恼:“早知道刚刚引开他们时就该把他们都杀光。”
顿了顿,又明朗起来:“不过现在杀光也是一样的。”
这未免也太轻敌了!
敌人将我们包围,安歌手提长刀,一刀一个,另一手还拉了一个左躲右闪的我,但是她冷静沉着,面不改色,砍人就如同切菜。
我瞧着这满目的刀光与剑影,简直大气也不敢出,眼见着侧面有个人提到向她砍去,恰在她视线的盲区,赶忙急道:“小——”
“心”字还没喊出口,安歌仿佛背后也长了眼睛,头也不回,反手就是一刀,刀刃便穿透那人的胸膛了。
她往前头又踢倒了两个,这才将长刀抽出,一时间鲜血喷涌而出。
我:“!!!”
那血喷得又高又远,我站得近,有几滴就落在我的脸上,又烫又腥。
我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!简直愣在当场。
莫说是我,就连那些来抓捕的官兵,都一时被震慑住,不敢上前。
安歌乐得得了这么个空隙,低声问我:“画皮师,会骑马么?”
这我倒是会的。
安歌于是指一个方向给我:“从那里走,百来步的树下,我留了一匹马。”
安歌道:“我一会儿将这圈子撕开一道口子,你去骑马,然后来接我。”
我大惊:“可是——”
没什么好可是的,安歌根本没给我反应的时间,带着我往她指的方向一撞,趁他们下意识躲避的时候,抬刀又砍倒两个,然后拿刀柄往我背后重重一拍,我就出了包围圈。
真是太虎了!
但是此刻箭在弦上,我迟疑不得,拔腿就跑。
没跑出几步,包围圈中分出两个人向我追来,眼见就要抓到我,那边传来啸啸风声,是长刀划破长空,将那两人串成串儿,当胸而过。
安歌将长刀掷了出来。
我眼见着那串儿在我身侧直挺挺倒下去,脚步未敢停,仓惶地回过头去,她掷刀的动作还没收回去,遥遥与我对视一眼,将头一点,转身与那些人肉搏。
6
这一夜实在是兵荒马乱。
我几乎跑出人生最快的速度,解了马匹、接了安歌又甩脱了追兵的时候,天光已经大亮。
我与安歌共乘一匹马,又折腾了一夜,满身的汗臭味,还有更浓的血腥气。
原本我们是在逃命,前胸贴后背也是迫不得已,这会儿终于脱了险,骤然松懈下来,再考虑我们这个姿态,就很是不妥了——
安歌她,近乎是把整个人都靠在我的胸膛上了!
有风起,吹起她的发丝,拂过我的面颊,我顿时局促起来:“他们追不上了,歇会儿吧。”
安歌哼哼两声,没说话,也没动,仍是靠着我的胸口。
四下里又寂静,怪让人觉得不好意思的。总得找点什么东西填满这寂静。
我想了想,道:“安姑娘,你让我先去骑马,如何能笃定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呢?”
我道:“要是我一个人纵马跑了,你岂不是身陷险境?你——”
正说着,安歌忽然在我怀里动了动,侧过脸来。
我说话时习惯看着人,她忽而抬眸,我的目光躲闪不及,一眼望进她的眼底,不由得一愣,不知为何想起来,大约是在几年前,我曾见过这样的眼神的。
那可不是什么山猫小鹿,那目光炯炯的,分明是一只神气抖擞的小豹子。
我猝不及防与这样的眼神一对视,惊得心跳都几乎要停了,话到了嘴边却一时止不住,呆滞地将后半句话说完:“——你为何愿意相信我啊?”
安歌看着我,我亦看着她。过了半晌,她却没回答,只道:“此处还不能保证安全,再往前走十里。”
顿了顿,又道:“我睡一会儿,到那时叫我。”
说着,靠回我的怀里,将双目一闭,就开始养神。
我简直手忙脚乱,又不知该忙乱些什么——
安歌虽说身手极好,但毕竟是个小姑娘,做武器的长刀又为了救我脱了手,虽说结果是有惊无险,到底受了伤。
我因此不敢纵马,只能小心翼翼地曲起双臂将她圈在怀中,缓慢前行,如此,也不知过了多久,我们前头终于横了一条溪流的时候,安歌也醒了。
她也不看我,跳下马去,俯身到溪边,先洗了把脸。
我抱着她的长刀去拴马,一回身看到她正扯衣领。
7
非礼勿视。
但她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。
我尚来不及转开眼,就见着安歌将衣领顺着右肩褪下来,那衣服的布料被从手臂的烂肉上撕下来,她眉头也不皱一下。
我瞧见那伤口,喉头一梗,顿时就移不开视线了。
她的动作很是娴熟,先是鞠了几捧溪水洗了洗伤口,然后干脆利落地撕下一段衣摆,咬在嘴里就要包扎。
我不由得出声道:“你……”
她嘴里还咬着碎布,不方便说话,只抬眼望着我。
我道:“你就这么直接包扎吗?”
她不说话,只冲我眨眨眼,一脸“为何不可”。
我不由得叹一口气,走上前去,将她嘴里的碎布拿下来,想了想,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:“至少,要先上点药。”
那一小瓶是金疮药粉,止血的效果极好,只是直接往伤口上撒,终归会有些疼。
但是安歌并不怕疼,她甚至并不看自己的伤口,只侧头看着我,目光炯炯,像一只专注的小兽。
我叫她盯得耳根有点烫,解释道:“我被抓的时候,担心他们对我用什么酷刑,时间又急,就只来得及抓这么一小瓶药。”
我避开她的眼神,犹豫了一瞬,又从怀里摸出了一块帕子,撒上药粉替她包扎。
安歌的皮肤并不光滑,但是白得很,两相对比之下,那伤口虽算不上深,可也显得怪狰狞的。
我心中很不是滋味,想了想,又忍不住道:“安姑娘,其实你何必来救我呢?”
我拿手帕在她手臂上打一个结:“虽说确实是你害得我身陷囹圄,可我们不过是卖家与雇主的关系,这世道人心不古,就算你不来救我,我也是理解的。”
她不答话,只是侧头看了我半晌,只看得我面颊都烫起来的时候,她忽而收回视线,一边整理衣服,一边道:“走吧!”
这转折突如其来,我一时没反应过来:“啊?去哪儿?”
她起身,将长刀一背:“西疆。”
8
半个月前,如果有人告诉我,我此生将参与刺杀当朝七皇子,还是参与两次,我肯定是不会信的。
安歌告诉我,十来天前她去刺杀七皇子,很可惜没能杀死他。好在她杀人不光用刀,也用*。
七皇子中了*,而能解这个*的神医恰在西疆,所以身中剧*的七皇子早已在几日前启程,如今,应当已经身在西疆了。
安歌道:“我总能杀死他的。”
所以她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,因为她还要继续刺杀七皇子,就还要我给她画皮啊!
这世道果真还是人心不古!
我不知她与七皇子有什么深仇大恨,但我本是个艺术生,这种打打杀杀的事,不是我所擅长的。
我也曾试图拒绝,我向安歌作揖施礼:“那就预祝安姑娘,马到成功了。”
她不承我的祝福,只看着我,面上是个似笑非笑的神情:“你先前是不是问我,为何只有一匹马,我却愿意信任你?”
我没明白她突然提到这个事的意图。
安歌轻笑一声:“因为就算你跑了,我杀光那些人,再来追你,也不是追不上。”
我还能说什么呢?我根本没得选!
那边安歌背着大刀已经跨上了马。
我望着她飒爽的身姿,不由得冲她的背影喊:“那你总得告诉我,你跟七皇子到底有什么仇怨吧!”
安歌身形一顿,侧着脑袋想了想,回头看我:“因为……他要娶我?”
安歌点点头,赞同自己:“他要娶我,我却不想嫁给她,所以我要杀了他。”
惊诧间安歌已经策马到了我身边,微微俯下身,向我伸出左手:“走吧。”
9
我与安歌同行,一路往西疆去。
我们都是朝廷通缉的要犯,客栈不敢住,大路不敢走,一路都是风餐露宿,条件很是艰苦。
我头几日还能忍,可毕竟是个艺术生,时间一长,难免憔悴。
这一夜守夜时没忍住打了个盹,一睁眼,身边多了道人影,是安歌。
安歌瞥我一眼,挑眉:“不行就去睡一会儿。”
她一介女子,尚且不会喊累,而我身为男子——男人不能不行!
我不屑地冷哼一声:“我还曾在极寒的北地服役一年,这点苦怎么能算得上苦呢!”
说着偷着眼去瞧安歌的反应。
安歌没什么反应,只是在火堆旁抱膝坐着,下巴枕在膝上。
她的夜行服早就换下来了,但仍是穿一身黑衣,这样缩起来坐着,瞧着只有小小的一团,偏偏目光凝在火堆上,瞳仁中倒影出两丛跳动的火苗。
不知怎么的,我就想起几年前,那时我还生活在盛京。
有一回京中权贵欢宴,一位公子哥曾向大家展示他猎奇所得的一只豹子。那是一只尚且年幼的雪豹,但是皮毛雪白光亮,目光犀利,很有精神。
此刻的安歌,瞧着比那只小豹子还要更有几分生气。
我心中一动,不由得道:“安姑娘,嫁给七皇子……不好吗?”
她侧眼看我,我便有些仓皇,想了想,补充:“至少,不用像现在这样辛苦。”
这其实也是这些日子我一直想问的问题。安歌不爱说话,可也没有兴趣遮掩自己的过去。
这些日子我与她同行,嘴巴不能得闲,一路上也旁敲侧击向她打听过七皇子,她虽然都答得惜字如金,可也算直言不讳。
于是我也得以在这些只言片语当中,拼凑出她和七皇子的过往。
安歌被七皇子选中,是在一个格斗场上,在此之前,她是十四楼星垣营的一个暗影;更早的时候,她则是林间的一只小兽。
她被遗弃在山林里,从小和野兽一起长大,后来被人路过捡到,因为兽性重、眼神凶,很适合做暗影,就被送进了十四楼。
当年高宗在位时,上阳长公主立十四楼,培养暗影,专为帝王行秘辛事,也正是因此,长公主薨逝之后,高宗赐其谥号为“昭”。
十四楼中多门类,入十四楼者,先入星垣营,然后根据所长,经过选拔进入各营。
安歌刚入十四楼的时候,甚至不会说话,但胜在天赋好、悟性佳,不过几年,就已成为最优秀的二流暗影——
只要再经过选拔进入千机营,便能跻身一流。
但她没来得及完成这一场选拔。
10
“我当然很优秀,”安歌顿了顿,“不过能参加选拔的,自然也都不是普通的暗影。”
我瞧她一脸不甘心:“所以你输了?”
安歌摇摇头:“我天生不知道什么叫输,所以与人相持,双方都伤得很重。”
七皇子便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。
选拔暗影的竞技场透光差,一整个场地有一大半被罩在阴影里,全是灰色的,偏偏七皇子穿了纤尘不染的一身白,连靴子也是纯白色的,撞进她的视线里,摸了摸她的脑袋,宣布道:“我要她。”
于是安歌没能成为千机营的暗影。
她成了七皇子的贴身护卫。
成了护卫,其实也和暗影没什么区别。
太子倒台后,朝中明面上平和,私下却分为两派。二皇子和七皇子成为太子之位的角逐者。皇子夺嫡,暗流涌动,她除了要保护七皇子的安危,有时也要去做些见不得光的事。
她身手好,但有时情况实在凶险,也不能保证全身而退,时常回到七皇子的府邸时,就带了一身伤。
七皇子亲自给她上药,有时拿拇指肚摩挲她结了痂的伤口,一双剑眉拧起:“安歌,伤在你的身上,可我的心也跟着痛了。”
他亲亲她掌心的伤口:“安歌,是你替我一步步挣来如今的荣耀与地位。将来我坐拥这江山,必定要立你为后。”
他说:“安歌,我爱你。”
听到这里,我不由得冷笑:“花言巧语。他若果真爱你,难道还会让你去冒这些险?”
安歌偏头看我,面上很是平静:“可是瞧见我身上的伤,他难过得甚至落泪。”
“鳄鱼吃人的时候,也掉几滴眼泪呢——那后来呢?”
“后来。”安歌道。却许久也没个下文。
我觉得奇怪,侧过脸去看她,却发现她正盯垂眸看着自己的右臂发呆。
那里是我前些天替她包扎的帕子,这些天她的伤其实已经好多了,换了几回药,帕子却一直扎在那里,上头绣着一只黑色的小豹子,一双眼目光炯炯,瞧着栩栩如生的。
她将帕子取下来,捏在手里看:“七皇子送过我很多帕子,但上头绣的不是花就是鸟,从没见过绣豹子的。”
“不过是突发奇想,随手画了底子叫人描了绣的,”我顿了顿,忽然有些不好意思,只好侧头看向远方,装着不在意的样子,“你要是喜欢,就送你好了。”
安歌没说话,只将小豹子的一双眼睛捏在手里摩挲,良久,才又开口道:“后来他等不到坐拥天下的时候了,他求我去帮他做最后一件事,他说等做完那件事,便和我成亲。”
我想起她之前说过的话来:“……所以你就跑了?”
安歌摇摇头:“其实和他成亲也没什么,做了七皇妃,俸禄比我在十四楼时还高一些。”
我明白了。
安歌还是个小孩的时候,就活在野兽堆里,后来让人给捡着了,也是丢进了如同养蛊场的十四楼。
她可以凭着动物的本能对爱有一个清晰的感知,却并不明白成亲对女孩儿而言是一桩什么样的大事。
我道:“那你为何——”
“因为我答应了替他做那最后一件事,结果害死了我的一个朋友,”安歌说着看着我,“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,我说我认识一个话多的人。”
我一愣。
那时还在风筝渡,我让她拿一个故事来换我的一张画皮,她说她认识一个话有点多的人,后来不见了,也可能是死了。
安歌道:“他是有点聒噪,可是并不讨人厌。我……实际上很是喜欢他,可是我将他害死了。”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baozia.com/nrly/12913.html